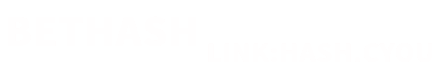
HASHKFK
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以《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克林贡语(Klingon)为例,已经有一些人学会了如何使用这种语言。克林贡语标榜其异质性在于独特的语音系统和罕见的句法结构,却依然像人类语言那样包含名词、动词以及主语、宾语等成分。其他虚构语言也不例外,如《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多斯拉克语(Dothraki)、《阿凡达》(Avatar)中的纳威语(Na’vi)以及《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昆雅语(Quenya)等。
在虚构作品之外,人类同样缺乏想象力。为虚构作品或其他目的而诞生的人造语言(constructed language,简称“conlang”)主要取材自语言学。但作为一门科学,语言学(linguistics)通常致力于探寻真实存在的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涵盖语音、符号或手势、语法、句子成分及语义表达等。尽管人造语言有的拥有别致的词汇体系,或刻意违背人类的某些语言规则,其创作本质上仍只是在改编地球常见的语言。
第一层面是符号,即人类生成、感知或交换信息的载体。我们用发声器官发出的声音是符号、你此刻阅读的文字是符号,表情包或禁烟标识等象形图、字母或古埃及象形文字等表意文字以及手语中的手势也属于符号。其他生物基于自身的生理结构,可能演化出比人类更丰富的符号系统。比如,非人类动物的语言并不复杂,其符号却囊括了气味与肢体动作;机器也能使用符号,人工智能之间用来交互的语言“GibberLink”中的高频声就是典型案例。
词汇还具有内部结构,可以通过后缀或其他形式标记格(case)、时态(tense)、数(number)、性(gender)等,中文中也存在通过偏旁部首来猜测生僻字的方法。句子也是如此,英语中句子通常为主语-谓语-宾语结构,而梵语句子则是主语-宾语-谓语结构。回到之前的例子中,如果把“insect”(昆虫)变为复数时将“-s”作为前缀而非后缀,就违反了英语的词法规则;如果说“Eat insects peacocks”(吃昆虫孔雀),则违反了英语的句法规则。
第四层面是语用,它关乎语言使用者如何表达字面之外的隐含内容。比方说当有人说“我饿的能吃下一头牛”这句习语时,是在表达饥饿而非真的想要吃掉一头牛。或者是那句著名的“”或者“华盛顿需要知道这件事情”,此处的“休斯顿”、“华盛顿”是一个转喻,它们指代的分别是NASA的载人航天控制中心和美国政府,而非这两座城市。有时,语用现象让我们能够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传递信息。打个比方,如果有人邀请你跳舞,你回答“我有舞伴了”比直接说“不”更有礼貌。这种“言外之意”及隐喻、转喻均属于语用现象。
更精密复杂的方案是构建一种打破人类语言常规结构的外星语言。人类不同语言在词和句子结构上本就存在差异。例如,在表达相同的一句话时,有些语言使用前置介词(prepositions),有些语言则使用后置介词(postpositions)。而表示特指时,有些语言有专用词(比如英语中的定冠词“the”),瑞典语之类的语言则使用后缀(比如“Vetenskapsradet”意为瑞典研究理事会,后缀“-et”表示特指)。不同语言中的句子语序也有差别,大多数语言在基本语序中都以主语作为句子的开头(如“我”、一个名称或名词短语“那只老虎”之类的指称性成分),但极少数语言会以动词开头。*
外星语言也可能只有一个类别,对应着人类语言中通常存在的两种或多种语法类型。有人声称,有些人类语言也只是“合并者”,即它合并了多个语法范畴。例如,北美西北部的萨利希语系(Salishan languages)被认为没有名词/动词的区别,而秘鲁安第斯山脉使用的克丘亚语(Quechua)则被认为没有名词/形容词的区别*。这些说法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它们让我们更有理由摒弃那种“外星语言的词汇应该属于人类语言词汇所具有的相同语法类型”的简单化假设。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种语言,其中所有词都属于同一类,因而无法被归入不同的语法类别。关于这种语言,哲学家们已经琢磨了一段时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其《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 中,提议一种逻辑上完美(logically perfect)的语言,其基础语句仅包含简单符号,类似于指代个体、物体和地点的名称如罗马斗兽场(Colosseum)或波哥大(Bogota)。维特根斯坦认为,当语言中的句子所包含的名称组合正确地“描绘”或代表了世界时,这些句子就是真实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包括属性和关系的世界本身就是由物体以不同配置方式组成的巨大集合。但即便我们不认同维特根斯坦这种关于世界本质的观点,我们仍能设想逻辑语言可以再次通过名字序列来表示事实。或者,逻辑语言也可以通过名字之间的不同距离,或句子中名字的不同空间排列方式来表示这些事实。无论作何决定,这种“维特根斯坦语言”(Wittgenstein languages)都是合理的候选语言,其词汇都属于单一语法类型:名词。这种合理性意味着外星语言也可能如此运作。
尝试联想一些非语言的表征系统,或许能帮助我们想象这些外星语言的语法类型。比如,相比于英语、斯瓦希里语(Swahili)或粤语,一门外星语言甚至可能更像某种地图。将地图上的各种元素识别成词汇或句子并非易事。当你在地图上看见一座教堂,有人可能会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名词短语“教堂”。然而,地图要素的属性与已知语言要素的属性有很大不同,无需语言描述,我们就能从地图上能同时看到教堂所处的空间位置信息。那么,为什么外星语言不能像地图一样,能同时表达教堂这个概念以及它的相关信息(例如名称、坐标、历史等等),或者能实时更新“我”和教堂的实时距离信息呢?
对人类而言,在符号或结构层面与人类语言存在差异的语言看起来注定会十分陌生,但其仍有可能被翻译成英语之类的通用语言。这类陌生的语言或许包含一些与某些英语单词或句子所指对象相同或表达相同意思的成分。例如,在维特根斯坦语言(Wittgenstein language)中,若将名字之间的空格代表“是……的老师”这一关系,那么“Aristotle Plato Socrates”(直译为“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 苏格拉底”)这样的句子可能与英语句子“Plato is the teacher of Aristotle, and Socrates of Plato(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意思相同。而地图上一片绿域中间有一个教堂的图标,就可以翻译为“教堂位于公园里”。 也就是说,若两种语言仅在基础形式层(如语音/文字)与结构层(如词法/句法)存在差异,而深层语义一致,那么它们的元素就可能成为互译项。
但如果一门外星语言与人类语言在深层语义层面存在差异,便会引发可译性问题。这会导致一种语言中的某种表达可能具有另一种语言中任何一种表达方式均无法表达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人类的不同语言之间也会出现不可译的情况。一种人类语言可能存在一个名词或动词具有另一种人类语言中没有的含义。譬如说英语的人很难找到德语“Fernweh”(一种渴望去远方的忧郁之感)的对应译文,就像我在自己的母语印地语中同样找不到英语“serendipity”(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幸运,来源于波斯语中对斯里兰卡的称谓)这个词的对应词语一样。
我们可以设想外星语言也会引发这类问题。外星语言中的某些要素可能无法翻译成人类语言,比如它们可能指涉某种独特的外星情感或某些外星人已发现而人类尚未发现的天体。不过,从原则上讲,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种语言中的名词或动词所描述的对象或现象,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若干词语组成的短句来描述。此外,如果我们尚未发现外星语言某些要素所描述的对象或现象,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索,从而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创造新的词汇或短语来描述它们,如此一来,这些新词汇便在我们的语言中成为外星语言要素的对应翻译。
如果有进化方式和感知方式都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外星物种,那该怎么办?外星物种的语言会反映其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这些分类是我们认知能力所无法掌握的。除非我们事先知晓外星语言中的某个片段对应着世界当中的何种要素,否则即使在我们的语言中创造一个新词也无济于事。这种外星语言的要素是根本无法翻译的,不是因为我们无法知晓它们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具有何种类型的含义。在《外星结构》(Alien Structure,2024)一书中,哲学家马蒂·埃克隆德(Matti Eklund)指出,这种不可译的语言确实可能存在,且无需诉诸认知机制差异来论证。
我们或许还可以尝试在人类语言中寻找与外星概念最接近的同源概念。一个有趣的类比是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质量”(mass)这一概念所做的分析。他认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质量”的概念进行了如此大的改动,以至于它们与牛顿质量(Newtonian mass)的概念互不相容也无法相互“翻译”(牛顿意义上的宇宙质量是恒定的,而爱因斯坦意义上的质量可以与能量相互转换)。然而,既然我们依旧能够同时理解爱因斯坦和牛顿的物理学,我们也有理由对理解外星语言所表达的概念抱有希望,尤其是当差异不是太极端、太普遍的时候。
假设存在这样一种外星语言,它在前三个层面与英语完全相同,但形成了不同的隐喻、转喻体系及交际规范。那么他们高兴时可以说“吃一匹马”,还会用“一只鸡”形容跑起来晃晃悠悠的个体。此外,相比于人类语言有言外之意,能传递超出字面含义的信息(前文那句“我有舞伴了”就委婉地拒绝了跳舞的邀约),这种外星生命另有一套交际规范,由此产生的言外之意也自成一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了解了外星人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才有可能参透只言片语。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机器之间基于因果关系的交互作用。比如你现在使用的设备与网站服务器之间发生的因果交互,才能将这篇文章投映在你的屏幕上。但这种交互能否算作语言交流?一种缺乏语义的语言还称得上是语言吗?这些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但在思考外星生命的交流方式时却无法回避。与外星生命相遇必将挑战人类对于身体、意识、生命以及智慧的认知。而语言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既然如此,我们不是更应该竭力探索那些与人类语言截然不同、甚至可能颠覆语言定义的外星语言吗?